弘一大师与广洽法师
发布时间:2019-11-15 09:42:11作者:楞严经读诵网一九二九年一月(夏历戍辰十一月),弘一大师在沪编就《护生画集》,写完序言交付上海开明书厂印行,便发愿随同尤惜阴居土,从上海乘轮同赴泰国弘法。轮船经过厦门,大师因身体不适要求登岸休息,准备恢复体力再行启程。承俗友陈敬兴南洋爱国侨领陈嘉庚胞弟接待,先在陈嘉庚公司集友行小息,复被介绍去五老峰参访南闽甲刹南普陀寺。最终被寺中诸师至诚挽留,盛情难却,弘一遂放弃原定海外弘法计划,留居厦门四月。是谓首下厦门。弘一大师与广洽法师也就在这一特定环境相识。
广洽(一九O一至一九九四)俗名黄润智,福建惠安田中乡人。五岁丧父,十岁亡母,举目无亲,孤苦伶仃。为谋生活,未及成年,他便从事各种劳役。因念生命无常,始茹素礼佛。一九二O年离开老家,独自去厦门求职,殊不料又因茹素被拒门外。生活无著,又走投无路,乃改而投奔南普陀寺,发心离开红尘世界。翌年礼瑞等上人落发出家,法名广洽,号照融。一九二二年去莆田广化寺受具足戒。因待人和善,又善于当家理财,故于一九二五年起,先后任南普陀寺知众、创寺,历时九年。一九三七年抗战后,侨居新加坡。历任新加坡佛教居土林导师,龙北寺住持,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,由于夙好写画,在寺接待宾客,因此广洽恭名弘一已久,了知弘一出家前乃无所不为的名艺术家,了知弘一出家后乃发愿重振南山律教的高僧,奈何迟迟无缘会面,只闻其名,不见其人。因此,知弘一前来南普陀参礼,广洽内心无限欢喜。为了抓紧机会向弘一请益,不顾自己身患咯血症居寺静养,自告奋勇照常履行知宾之职:先是主动陪同弘一参访南普陀大殿厅堂,接着随侍左右听候调遣,复又代为接待来访善信,直至会同寺诸师勤请大师留滞厦门,放弃海外弘法的原定计划。
广洽法师与弘一大师之相识,完全出于偶然。广治法师二次函请弘一大师三下厦门,则完全出于有的放矢。
第一次是一九三一年四月。弘一在上虞法界寺大病初愈,便接获广洽来信函请三下厦门。五月一日大师允缓访。表示至迟于中秋节返法界寺,料理一切,便可乘轮起程往厦门亲近慈座也。孰料中秋未到,日军已在沈阳制造“九·一八”事变,中国人民面临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。因为同年十月大师自温州抵达上海准备乘轮如期南下厦门时,沪上缁素诸友闻讯赶来恳劝大师时局不宁,务期暂缓动身。不得已,大师只能据此复信广洽说明原委。表示“倘有因缘”,来年当来厦门,亲近慈座也。一九三七年三月,弘一在南普陀佛教养正院宣讲《南闽十年之梦影》时云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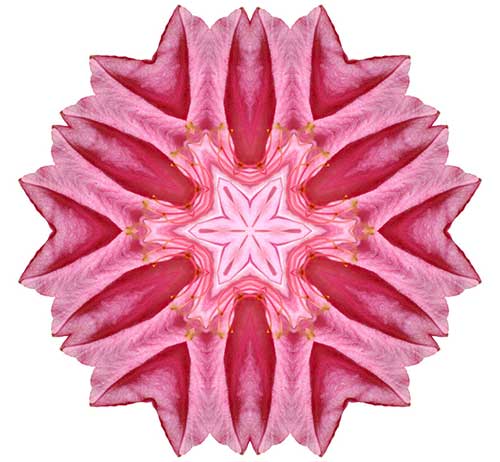
民国二十年九月(公历应为一九三一年十月),广洽法师写信来,说很盼我到厦门去。当时我就从温州到上海预备再到厦门,但许多朋友都说:时局不大安定,远行颇不相宜。于是我只好仍回温州(庆福寺)。
第二次是一九三一年十月,根据弘一前信之许,弘一在厦门南普陀足足等待一年之后,再次去信温州庆福寺,劝请大师履行前约:“倘有因缘”,来年当来厦门,亲近慈座也。要求大师起程三下厦门。面对广洽的又一次至诚礼请,弘一再无任可理由迟延,三下厦门再次提上日程。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弘一写信预告广洽云:
拟于十天后,搭乘新镒利轮往厦。但此舱无有定期,或延迟亦未可知也。不巧发信当晚,大师突患痢疾,腹泻不止,眼看预定行期无法起程,当月十五日,弘一又就此据实函告广洽云:
广洽法师慈鉴:前寄函想已收到。吾自十四日(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一日)夜间,急痢疾,至今未愈。倘近日可以全愈,即搭次班新镒利轮船往厦。倘一时未能全愈复元者,则更须延期也。所带行李不多,乞座下勿至码头迎接。因病犹未痊,动身之日难确定也。知劳远念,谨以奉闻。顺颂法安!
演音和南
所幸十一月二十四日痊愈,大师即自温州乘上新镒利轮,于十二月二日如愿三下厦门,暂居妙释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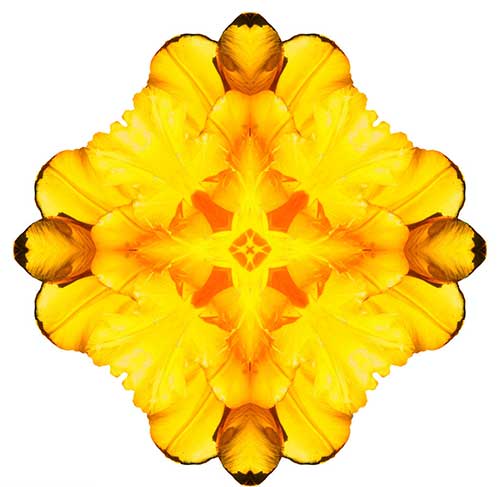
综上所述,再参阅有关资料,可知促成弘一大师如愿三下厦门,因缘一是由于性愿法师的至诚迎请,二是由广洽法师的二次函请。两人合作默契,善始善终,异曲同工,如愿有成。再加上广洽性愿所作的种种努力,因而自三下厦门之日起,弘一大师便受到“种种礼遇”:衣食丰足,诸事顺遂;二,专心著述,无后顾之虑。故自一九三二年起,弘一曾多次辞谢挚友夏丐尊北返上虞白马湖晚晴山房之约,留居南闽十载,直至温陵终老。弘一大师与广洽法师也结下诸胜因缘。(信息来源:摘自《十方》)
编辑:明蓝






